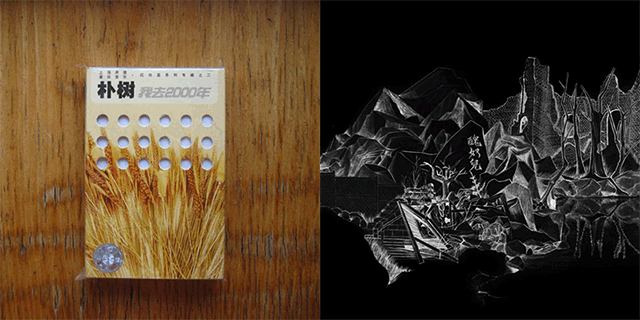
从2000年到2017
2000年,千禧年。一个时间节点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的意义:乐观、平和、富足,不一而足。人们怀着普遍的乐观主义去看待新纪元的开始。就像多年前梁漱溟回答他父亲“这个世界会好吗”的问题时,用的是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”那种乐观。
朴树似乎怀疑这种乐观。于是他在《我去2000年》里用戏谑、嘲笑来怀疑,怀疑的对象从自己到被号称为新纪元的生活,怀疑自己和世界是否会变得美好。但同时,朴树又不忍心太过于绝望,劝着自己的同龄人:“关于未来,请你坦然,不要离开”,而且也不忘激励自己“我是金子,我要闪光”。
到了2017年,已经没有人再去问”这个世界会好吗“这样的问题。因为答案就写在网络上:世界在往糟糕里转变——书本上/纲领里所应许过的美好变得虚无,不管怎么样的价值观都像一出骗局,生活似乎更为艰难:工作压力、环境问题都扑面而来。用以对抗这些艰难的,是我们厌恶的鸡汤还是同样性质的毒鸡汤?
“草东没有派对”(下称草东)站了出来,也同样怀疑着自己和这个时代是否会变得美好,但他们不是揭穿这虚无和骗局,而是单纯表达愤怒、无力、虚无,最终指向的是自嘲与不屑:“请别举起手枪,这里没有反抗的人”、“ 你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?那东西我们早就不屑啦”。
从2000年到2017,从朴树到草东,同样的青春似乎从“不乐观还不至于绝望”到“无所谓的绝望”中滑落。

▲ 朴树
从嘲笑到自嘲
从豆瓣对朴树的访谈开始,他的形象在我所在的社交世界里处处刷屏。根据“你所关注的,都是你所选择的”原则,朴树的视频、新歌,在社交上帝(Social God)看来,我就是他的完美受众。
尽管如此,我依然没有兴致点开他的视频、新歌。因为纵观《我去2000年》之后的朴树,我宁愿在记忆里只保留2000年前后的他的音乐。
究其原因,我怕朴树会变成他嘲笑过的人——在《我去2000年》中,朴树嘲笑那些“后来摔了跟头,老了,就变得谨小与甚微,就忘了梦想只乞求能够平安地活着”的中年人。如果真的如此,那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碎?
然而草东似乎没有这些顾忌——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里,就尽情地嘲笑着自己。
草东嘲笑自己,“原来自己那么丑陋”,顺带表述了“他们扔了你的世界,去成为更好的人类”(《勇敢的人》),就像一句“废人宣言”,更像是对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人说,让他们去吧,我们不是一类。这个姿态,以至于台湾的乐评人/媒体人把他们当成了鲁蛇世代的代言人。鲁蛇何物?就是英文Looser的音译。
写到这里,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当年花儿乐队。那时期的大张伟尽管还未成年,但却堪称最年轻的朋克,到如今,他的朋克只剩下发型。
当然了,如果要避免心碎,我们最好的武器,就是嘲笑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▲ 草东没有派对 乐队
八度的悲伤与无力
在听草东的时候,总让我一度想起朴树。开始的时候,我以为是他们都是那种“欢快编曲但配以不那么欢快的歌词”的风格,就像语文老师常告诉你“乐声写悲”的强烈反差那样。
但这个理论在缺乏乐理的支撑。
然后就是朴树和草东主唱的声线的相像:他们在低音的部分的演唱方式,如果不看他们的照片,你会不会想象着他们应该都是有着青春痘的青年?
朴树清泠泠地唱“大家醉了,就我醒着,我真傻”,那种被压低了八度的声音,就是怕被人听到似的。在很多歌的前半部分,草东也是用低八度的、仿佛压抑过了的声音在唱,而几乎每一次,都会迎来高了八度的结尾。
究其原因,在人们高声、欢快地乐观奔向2000年的时候,只要清泠泠的歌声就足够让人听到青年的不同。但在无望而雾霾重重的现在,青年们必得以高八度的声音才能与时下“现世安稳、静好”划出清晰的分界线。
那么,从朴树到草东,不变的或者只是青春的悲伤与无力。
青春,悲哀都一样同
不管媒体或先辈们用各种形容词堆砌到90后身上都不奇怪,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,“谁没有经历过一无是处的二十几岁”。如果日历往前再翻上十年,毫无意外的是,媒体和先辈们几乎是用同样的语气和词语来形容80后们。而这之间的惟一变化,大概就是在看起来越来越开放的互联网,反而是越来越压抑。世界的是与非原本还有一条分明的界线,现如今似乎更模糊了。谁也不知道,到底向左还是向右走。
“但那挫折和恐惧依旧”,二十几岁的青春,悲哀都一样同。
在去向新纪元的路上,朴树唱出那种迷茫、困惑、不解:新游戏、新的面具、新的规矩,“别当真,别多问,别乱猜,我没有答案”(《我去2000年》)。而在新纪元的第一个十年之后,草东说“我们在原野上找一面墙,我们在标签里找方向“(《我们》)。
17年前朴树说”在这儿每天我除了衰老以外无数可做“,现如今草东唱着”我们万分惋惜地浪费着“,这些情感似乎都不曾改变。
有一个故事广为传播:小时候最痛苦的游戏就是躲猫猫,因为自己躲得太好,谁也没找出来,就一直躲到天黑。这是一件童年所不能了解的事。
在《大风吹》里,草东有着变幻的叙述立场,除了“那种东西我们早就不屑啦”的第一人称之外,你是否会想起上述那个小时候的游戏一样,有着另一种我们所不能了解的孤独。
“一样的感觉,一样的屈辱”。
再过10年,你猜还有谁会用各种形容词来堆砌给那些二十几岁的年青人?不外都是三十、四十岁的90、80后们。
荒唐吗?悲伤是吧,没有办法,就祝我们都小康吧。
到底是我还是“他们”全疯了
在17年前,朴树还可以弹着吉他唱道”关于未来,请你坦然“,然后鼓励那些”不成熟的,快快地成长;成熟了的,都通通的开放“,感叹生命不长,“那些坏天气,总会过去”。这样既是出于自我安慰,也是出于对当时现实的映照。
带着对中年生活、现实世界的嘲笑和自我的迷惘,朴树只有低八度的呐喊“到底是为还是他们全疯了”。
故事似乎没有变得更美好,世界也更是如此。或者是出于此原因,嘲笑也好,痛恨也好,草东都把这些朝向了自身。理想、目标、退缩、懦弱、不勇敢、不努力、挫折、恐惧,高八度的“杀了我吧”。
而更为悲伤的是,朴树至少会在最后还会挣扎着说“妈妈,我是金子,我要闪光”。草东只是说“什么也没改变,什么也不改变”。
民谣不是赎罪券
中世纪晚期,罗马教廷为了筹集资金,开始授权神职人员四处贩卖赎罪券。据说,领受了赎罪券的人们的罪过就能获得神的赦免。从某种意义上看,这赎罪券更像是人生的万能锁匙。
面对人性的复杂情形,如果你在往下掉,世上是不存在“赎罪券”那样的东西的。在命运和不公面前,谁能祈求一张赎罪券就解决所有问题?
在新纪元的今天,没有这样的事。
所以,不管是那些劝人安分守己的心灵鸡汤还是硬币背面的毒鸡汤,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答案,因为丰富的人性有万千答案。
而不论是朴树的低八度呐喊,还是草东的疯狂自嘲,都只是青春在某一个片段里与现实的相互映照。就像《天堂电影院》中所说的那样,“电影不是生活,生活难多了”。
乐曲、歌词以及现场的跺脚、呐喊,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。如果把这一小部分当成我们所有的现实,那无疑是一叶障目,也无异于向命运寻求那不存在的赎罪券。